
要重视不同领域的创新规律,突破固有创新路径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近几年到一些城市交流时,科技部门的负责人常会提及我关于深圳科技创新路径的文章对他们的启发。这篇总结深圳过去40余年科技创新路径文章的核心观点是:深圳科技创新不是传统的所谓自上而下成果转化的模式,而是建立在市场需求基础上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有科技部门的负责人说,受该文影响,他们改变了当地科技计划的资助方式,从过去按照成果转化的逻辑重点资助体制内科研机构,变成了重点资助企业的技术创新。
看到自己的观点在行业里被接受,并且影响到一些地方科技政策的形成,自然是高兴的,但高兴之余我又对自己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深圳需求导向的科技创新路径能否作为中国科技创新的普遍规律推而广之?如果仅仅涉及市场化的企业技术创新这部分,需求导向的创新路径模式可以被作为普遍规律,但如果是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层面上讨论产学研关系,需求导向的创新路径并不能够作为普遍规律适用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行业和领域,科技创新路径模式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研究和总结这种差异性对于当下的中国科技界是一个紧迫的任务。不要笼统地说,科技创新是基础研究多一点还是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更重要一点,如果把不同领域的创新规律搞清楚,政府应该怎么配置资源?如何推动产学研合作?问题会变得相对清晰。
深圳需求导向的科技创新路径,主要表现在电子信息领域。电子信息领域创新的科学基础主要是基于物理、数学等基础学科,这些学科自20世纪以来并没有出现颠覆性的科学发现,相反在应用端,由于电子信息产品广泛而深入地植入社会经济、社会治理与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自需求端的变化成为推动创新的主要力量。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数十亿数字化人口参与创新过程,极大地改变了创新的范式,因此,应用端驱动的创新逐渐成为新的主流模式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领域都适合这个模式。以深圳为例,过去40多年,在生物医药领域,深圳没有出现沿着需求端成长为国际大公司的成功案例,即便医疗器械部分有些苗头,但那也只是深圳强大的IT产业的一些衍生品。有一段时间,深圳医药产业在规模上曾经居于国内前列,但始终没有出现国际性大公司,规模上也逐渐被长三角城市超越,我不得不承认,单纯依赖需求导向的路径不足以发展出国际领先的生物医药产业。生物医药领域的创新对基础研究的依赖性十分明显,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生物医药产业在基础科学领域还有太多未知需要去探索,不像电子信息领域,是在知识的天花板下创新,导致学科交叉、应用端驱动成为主流。对基础科学表现出高度依赖的领域还不限于生物医药,材料领域也有类似的现象。当然,并不是说,因为生物医药领域对源头创新有依赖性,这些领域就可以沿用过去的科研方式去部署基础研究,体制内科研存在的问题依然需要加以解决。
研究不同领域科技创新的规律,对当下政府如何制定科技发展战略,合理配置科技资源十分重要。近年来,在中美科技战的刺激下,各级政府急于寻找一条突破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途径,组建国家和地方的大型实验室是当下的常规做法,尽管政府设计实验室的初衷是想跟传统的科研模式做出区隔,提出了一些问题导向的科研目标,但在运作的体制机制上,并没有摆脱传统的科研模式,实验室队伍的组建方式还是依托那些玩科学的专家,只是换了一件马甲而已。特别是电子信息领域,中国大公司的创新能力已经是国际先进水平,很多大厂的能力远超体制内科研机构,在这种情况下,组建国家实验室还沿用旧的体制机制,完全没有必要,尤其是像深圳这样的城市。
有人会问,国家实验室是具有公共性的基础研究机构,跟大厂能力有啥关系?但大公司参与基础研究在国际上有很多成功的案例,面对中国体制内科研由来已久的各种先天缺陷,由大公司作为国家实验室的组织者可能不失为当下中国基础研究的一条可行路径。历史上,最著名的企业实验室首推美国的贝尔实验室,这个由AT&T创办的实验室在科技史上是近乎神一样的存在,以晶体管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发明、11位诺奖、16位美国最高科学和技术奖、4位图灵奖都产自于这个实验室。华为、中兴都是在学习贝尔实验室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公司。中国IT大厂的元老们至今提起贝尔实验室还是一脸的敬畏。回忆这段历史是想说,企业作为国家公共基础研究的参与者是有成功案例的。
前不久,我在一个城市看到了某大厂与地方政府合作组建的实验室,给我眼睛一亮的感觉。在这个案例中,大厂是实验室的组织者、运营者,实验室的定位、人才招募和日常管理都是大厂的团队负责,3年时间实验室已经规模化运营,给我最深的印象是:相对于很多国家实验室“不明觉厉”的存在,这个实验室通过大公司带入了产业问题,整个实验室的规划运营能够看到清晰的解决问题的逻辑和实现路径。如果这个实验室能够解决好知识产权的分享和开放性,不失为国家实验室建设一个重要探索。
这件事也引起了我对“大厂”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承担角色的一些联想:一些大厂应该作为国家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的组织者,在国家创新体系里承担更重要的职责,不要让市场经理去用PPT忽悠政府的订单,大厂卖产品的思路不能解决政府数字城市建设的真正需求,把这些场景留给小公司,以专注和敬畏的态度去打造新的商业形态。
创新理论研究的滞后是中国科技创新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政府的决策经常被一些似是而非的创新理论左右,导致政策的错配和资源配置的巨大浪费。现在,搞创新研究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贩卖国外的创新理论,这部分有一定参考价值,但照搬就容易出问题;二是诠释政府文件和领导讲话,很难称得上是创新理论。记得3年前一次论证会上,我说起需求驱动的创新路径,遭到一位来自985大学校长的批判,他很不客气地说我没有做好文献研究的工作,国家关于创新路径的说法只有“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三种模式,哪来的需求导向的创新?他把秘书班子的提法视为圣经,却不接受我对深圳数十年科技创新实践观察总结的表述,让我大为吃惊。从某种程度上,这也反映了中国科技创新理论研究的困境。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作者周路明系国家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深圳)总裁、深圳市源创力离岸创新中心总裁、深圳市源创力清源投资基金董事长]
标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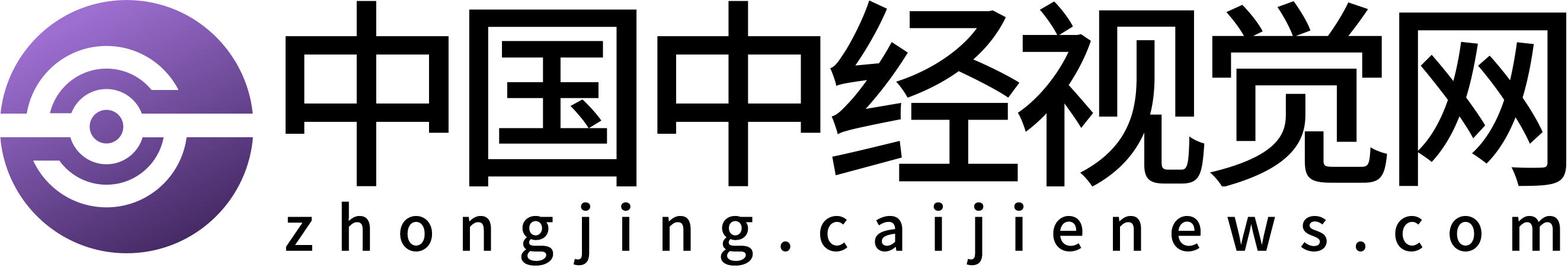




![[新基]广发积极回报3个月持有发行:基金经理曹建文掌舵 投资表现近一年-3.87%](http://img.kaijiage.com/2022/0610/20220610024838983.jpg)



